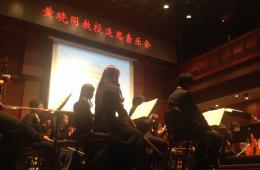原标题: “戈多”变成“果陀”笑过以后我们还有痛感吗?

2006年,吴兴国就曾带他的台湾当代传奇剧场在沪上演过一次《等待果陀》,此次是相隔近十年后《等待果陀》第二次登陆上海。
《等待戈多》,是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吴兴国,是以京剧形式改编西方经典著称的当代传奇剧场的创始人。这对上海的戏剧观众来说都并不陌生。资深的上海观众更不会忘记,就是近十年之内,贝克特的权威演绎者爱尔兰剧团就不止一次携此剧来沪,而吴兴国的《等待果陀》也至少是第二次登陆吧。但这一次,有什么异样呢?
今年正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全世界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纪念。不知是否有意安排,《等待果陀》演出之际正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那么,观众们是否也将这个戏和70年前的那场悲剧性的杀戮联系起来了呢?
对于一出戏剧演出,我们当然可以完全不了解任何背景,直接去看这个戏本身就会带给我们什么审美感受。但是,对于一出以京剧形式改编西方经典的戏剧作品,我们大多还是会关注:它改得如何?还是京剧吗?还有原剧的味道和旨趣吗?
显然,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京剧了,而只是运用了许多戏曲的程式动作、音乐、念白等手段;也不是原剧的简单译植,而是进行了高度本土化的改编。虽然故事的情节、结构、人物等都没有变化,但许多插科打诨的内容都是中国式的了。更有意味的是,和大陆将题目译作“等待戈多”不同,此剧译作“等待果陀”,是等待某佛教圣人,把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改成了中国的佛教背景。这一改动,意味大变。但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完整、成熟、有机的艺术品。
在西方戏剧发展的链条中,贝克特写于1952年、首演于1953年的《等待戈多》是一部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阶段的作品。它的形式已经开始在反语言、反情节、反人物、反逻辑了,但还有语言、有情节、有人物、有自身的逻辑。和传统的戏剧文学明显地拉开了距离,但又还没有像后现代戏剧那样放逐文学。它的内容则接续了现代主义鼻祖尼采以来“上帝死了”之后我们该如何是好的主题,是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以及现代科技文明的深刻反思。尤其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如果说萨特的存在主义还表达了人类试图自我救赎的积极而悲壮的努力,那么贝克特此剧则更多地笼罩着消极等待、无聊自弃的悲观厌世的气氛。
中场休息时,一位欧洲文化专家、也是对贝克特诗学有深入研究的前辈学者对我说,这是一部很成功的改编作品,但她感受不到原剧中那种浓浓的悲剧感和恐怖感了。也许是我们的观众对原剧产生的基督教文化背景比较隔膜,也许是吴兴国的改编就以京剧的形式和佛教的精神稀释乃至改变了那种氛围。我注意到剧场发出笑声时,正是京剧手段运用得比较集中时。那种有规则的自由运动、那种略带粗俗的捧哏逗乐、那种夸张的无厘头的谐谑表演,常常精准地击中了观众的笑点。而佛教的那种看破红尘、普度众生的随缘大度,也自然和基督教自赎原罪的严肃崇高感大不一样了。
成功的改编从来都不会是复述原旨,往往会融合改编者自己的生命体验,表达改编者的思考。此剧也不例外。吴兴国这一辈人虽然没有经历二战,但也是目睹了鼎革之变的沧桑阵痛的。他说他改编此剧的目的是献给他的母亲以及像他母亲那样经历了战争磨难的人们。“1949年,就有一大群人因战争从大陆迁徙到台湾,我的母亲就是其中流离颠沛、离家飘零的孤女。小时候经常看见母亲,坐在庭院的藤椅上,在黄昏暮色中遥望远方,就这样静静地,等待时间流逝,直到黑夜完全淹没了她,就这样,日复一日……”“每一出戏的选择都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不知怎的,《等待果陀》带给我很大的震撼,这个戏谈一个时代,甚至一个世纪的问题,而历史摆在眼前,人类却很失忆,那些因天灾人祸而受苦难的人已经被遗忘。”这是吴兴国在节目册里的告白。从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他选择在日本投降日演出此剧是有特殊意义的,也以为“果陀”的佛教意味更足以超度战争中的亡灵、抚慰未亡人的心灵,表达人类对和平的向往。